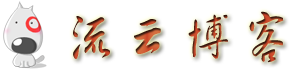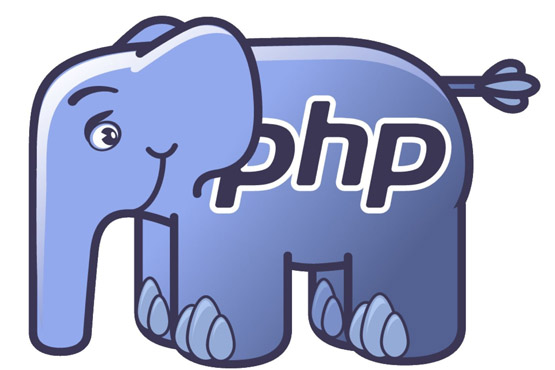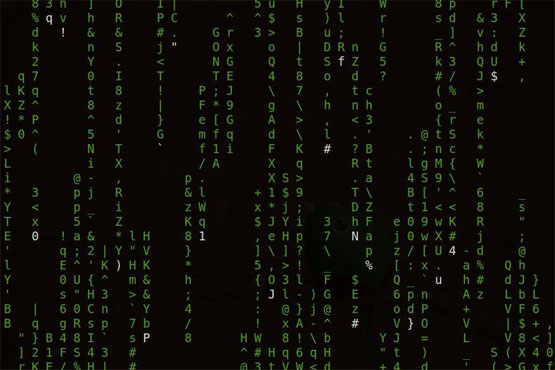大理的夏天是被阳光泡透的。万历年间的苏州也热,却多是黏腻的湿热,裹着河道的水汽往人骨头缝里钻;而大理的热是坦荡的,阳光像金箔似的铺在古城的青石板上,踩上去能烫得人踮脚,可只要躲进树荫,风一吹就带着苍山雪水的凉意,清爽得很。

沈复坐在“月明小筑”酒馆的门槛上,手里摇着阿秀编的蒲扇,看着街对面的白族阿婆在晒扎染布。蓝白相间的布料在阳光下舒展,像极了洱海的浪与云。他的手机放在腿上,直播后台还在跳动着回放数据——自从天鹅古堡探险后,他的账号粉丝已涨到十一万,评论区里满是催更的留言,有人问下次探险去哪,有人求他多讲点和芸娘的故事。
“三白!快别晒着了,进来喝酸梅汤!”阿秀端着个粗瓷碗跑出来,碗沿挂着两颗晶莹的冰珠,“老沙刚冰好的,加了蜂蜜,解腻又消暑。”
沈复接过碗,喝了一大口,酸甜的凉意从喉咙滑到胃里,舒服得他眯起眼:“阿秀姑娘的手艺越发好了,比芸娘当年酿的酸梅汤还多几分清冽。”
“那是自然!”老沙从里屋探出头,手里举着一把刚削好的火把,“再过三天就是火把节了,我这火把都备好了,今年要扎个三层楼高的‘火树银花’,保准让你开眼!”
沈复凑过去看,那火把由几十根松木捆扎而成,顶端缠着彩色的绸带,底部绑着四个木轮,方便推行。“这便是火把节的火把?某在明代时也见过上元节放花灯,却从未见过这般气派的火把。”
“那你可算来对了!”良源背着相机走进来,镜头盖还沾着点露水,“我刚去才村拍素材,家家户户都在扎火把,有圆的、方的,还有扎成麒麟形状的。晚上点燃后,整个古城都亮堂堂的,大家围着篝火跳大三弦,撒松香,热闹得能通宵!”
“可惜阿峰和阿丽去丽江了,说要拍雪山下的纳西族火把习俗,赶不回来陪你过节了。”阿秀叹着气坐下来,手里还在给蒲扇缝花边,“不过他们在群里发了红包,让我们替他们多吃点烧烤,还说等回来给你带丽江的雪茶当直播道具。”
沈复心里虽有几分遗憾,却也笑着点头:“丽江雪茶清冽,配着大理的梅子酒倒是绝配。既如此,咱们便替他们多尝些火把节的风味。”
“刚从古城门口买的,热乎着呢!”阿丽把纸包塞进沈复手里,“我们在西藏听牧民说,大理的火把节能驱邪祈福,特意赶回来陪你过。对了,我们还约了去看城南的火把扎制,那里有个老匠人,扎的火把能开出‘牡丹’形状的火,去晚了就看不到了!”
他拿起手机稳定器,“正好开着直播,带乡亲父老去看火把扎制,让阿峰阿丽在丽江也能云过节。”镜头刚对准街景,弹幕瞬间涌了进来:
“火把节!我去年去过!撒松香的时候超震撼,火焰会突然蹿很高!”
“沈公子快带我们去看扎火把!想知道这么大的火把是怎么扎成的!”
“阿峰阿丽去丽江了呀?丽江的火把节也很有特色!”
“没有峰哥阿丽也没关系,看沈公子和秀姐沙哥良源兄也超开心!”
“沈公子快带我们去看扎火把,想知道牡丹火是怎么扎的!”
“听说大理火把节有很多手工艺品售卖?”
沈复笑着回应:“诸位乡亲父老,今日某带大家去看火把节的火把扎制,还能见到会开‘牡丹火’的老匠人。大家跟着某的镜头,一起去瞧瞧这大理的特色节日!”
城南的空地上,早已摆满了待扎的火把原料。松木、柏枝、绸带堆得像小山,几位白族老匠人正围着一根粗壮的松木桩忙碌。最中间的是位头发花白的老人,手里拿着把弯刀,正精准地削着松木的枝丫,刀刃划过木头的声音清脆悦耳。
“李阿爷!我们来看您扎火把啦!”老沙熟稔地打招呼,他早年在城南卖过烧烤,和这位老匠人相熟。老人抬起头,看到老沙,脸上露出笑容:“是小沙啊,今年的‘牡丹火’我留了最紧实的松木,烧起来花瓣更挺括!”
沈复举着手机,镜头对准老人的手:“诸位乡亲父老,这位是李阿爷,扎火把的手艺传了三代了。您看他削松木的手法,行云流水,每一刀都恰到好处。”弹幕立刻刷屏:
“这手艺太牛了!现在还有这么厉害的老匠人,不容易啊!”
“李阿爷手上全是老茧,一看就是干了一辈子的!”
“牡丹火是什么?是火把点燃后会变成牡丹形状吗?好期待!”
李阿爷听到弹幕的声音,对着镜头笑了:“没错,这牡丹火是我们家的绝活。扎火把时要把柏枝摆成牡丹花瓣的形状,裹上浸了松油的棉纸,点燃后柏枝受热张开,就像一朵盛开的红牡丹。”他指了指旁边扎好的半成品,“你们看,这就是牡丹火的雏形,等下绑上绸带,就更漂亮了。”
良源蹲在一旁,拿起一根绸带,学着老匠人的样子往火把上绑:“沈兄弟,你也来试试?绑绸带要讲究对称,左边绑红的,右边就要绑绿的,这样点燃后颜色才好看。”
沈复放下手机,拿起一根蓝色的绸带,小心翼翼地往火把上绕。他想起明代时给芸娘扎花灯的场景,那时他也是这样,拿着彩纸一点一点地糊,芸娘在一旁给他递浆糊,笑着说他“手笨却心细”。指尖触到粗糙的松木,又想起芸娘的温度,他的动作慢了下来,眼神里多了几分温柔。
“沈公子在想什么呢?”阿秀注意到他的异样,轻声问。沈复回过神,笑着说:“想起了某的妻子芸娘,以前某给她扎花灯,也是这样小心翼翼的。”弹幕瞬间变得温柔:
“芸娘姐姐要是能看到现在的火把节,肯定也会很开心吧。”
“沈公子对芸娘姐姐真好,这么多年了还记着她。”
“突然有点想哭,这就是‘三白游记’里的深情吧。”
扎完火把,几人往古城回走。路边的店铺都挂起了红色的灯笼,有的店家还在门口摆上了火把的模型,上面写着“大理火把节快乐”。穿白族服饰的姑娘们提着小灯笼走过,绣花的围裙在阳光下晃出好看的弧度,引得路人纷纷拍照。
“前面有卖松香的!”阿丽指着路边的小摊,“撒松香是火把节的习俗,松香遇火会爆燃,能驱邪祈福。我们买几包,晚上篝火晚会用。”
沈复跟着阿丽走到小摊前,摊主是位白族阿婆,手里拿着个布包,里面装着金黄色的松香块。“小伙子,买松香啊?要多少?这是今年新采的松香,纯度高,撒出来的火又大又旺。”
“阿婆,来五包。”沈复接过松香,付了钱。阿婆笑着塞给他一个小香囊:“这是薰衣草香囊,火把节戴在身上,蚊虫不咬。你们是外地来的吧?晚上去洋人街看篝火,那里最热闹,还有白族的三道茶喝。”
回到“月明小筑”时,天色已近黄昏。老沙正在院子里搭烤架,旁边摆着刚买的五花肉和洱海鱼,香味飘得老远。“回来啦!快洗手,准备吃烧烤!”老沙喊道,“我还买了点杨梅酒,冰镇过的,配烧烤刚好。”
几人围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,烤架上的五花肉滋滋冒油,撒上孜然粉后,香味更浓了。老沙喝了一口杨梅酒,抹了抹嘴:“沈兄弟,明天火把节,我们先去逛古城的庙会,吃点小吃,然后去洋人街看篝火。三层楼高的篝火,点燃的时候超壮观!”
“还有跳大三弦的!”阿秀补充道,“白族的小伙子们会穿着民族服饰,弹着大三弦跳舞,姑娘们会唱着歌给大家敬酒,谁要是被敬酒了,就要喝三碗,不然就是不给面子。”
沈复听得心驰神往,举起酒杯:“那某可要好好见识一下,这大理的火把节,定比明代的上元节更热闹。”他看着眼前的众人,心里满是温暖——在这个四百年后的时代,他有了新的朋友,新的牵挂,还有了让他热爱的直播事业。只是偶尔,当风掠过院子里的梧桐叶,他还是会想起芸娘,想起苏州的雨,想起那些“布衣菜饭,可乐终身”的日子。
火把节当天,大理古城从清晨就热闹起来。沈复刚打开直播,在线人数就突破了1万。他穿着阿秀给买的白族对襟衫,戴着蓝色的包头,手里举着个小火把,镜头扫过古城的街道:“诸位乡亲父老,今日是大理的火把节,咱们四个陪大家过节。大家看,街道上已经挤满了人,家家户户都挂着灯笼,是不是很热闹?”
弹幕里全是羡慕的留言:
“羡慕哭了!我也好想去大理过火把节!”
“沈公子穿白族服饰好好看!有古代文人的气质!”
“前面有卖乳扇的!沈公子快去买,我想吃!”
阿秀拉着沈复走到一个小摊前,买了一串烤乳扇:“快尝尝,这是现烤的,裹了蜂蜜,甜丝丝的。”沈复咬了一口,乳扇的奶香混着蜂蜜的甜,在舌尖散开,好吃得他眼睛都亮了:“果然名不虚传!比某在明代时吃的奶酪还香。”
逛到中午,几人去吃了白族特色的八大碗。酥肉、粉蒸肉、洱海鱼摆了满满一桌,老沙给沈复倒了杯米酒:“这是白族的三道茶里的甜茶,用糯米酿的,度数不高,喝着暖胃。”
下午时分,古城里的人越来越多。小伙子们扛着扎好的火把,在街道上穿行,火把上的绸带随风飘动,像一道道彩色的虹。穿白族服饰的姑娘们提着花篮,给路人分发鲜花,整个古城都弥漫着花香和烟火气。
傍晚时分,几人来到洋人街。这里早已搭起了一个巨大的篝火台,三层楼高的火把矗立在中央,顶端缠着金色的绸带,底部摆满了松针和柏枝。周围挤满了人,有本地的居民,也有外地的游客,大家手里都拿着小火把,脸上洋溢着期待的笑容。
“快看!要点火了!”阿丽指着篝火台喊道。只见李阿爷手持火把,慢慢走上篝火台,周围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。他举起火把,对着天空喊了一句白族语,然后将火把凑近篝火底部的柏枝。“轰”的一声,火焰瞬间蹿起,沿着松木往上蔓延,很快就吞没了整个火把。
“哇!”人群爆发出一阵欢呼。火焰越烧越旺,橘红色的火苗跳跃着,映得每个人的脸上都暖洋洋的。李阿爷扎的“牡丹火”果然名不虚传,柏枝受热后慢慢张开,真的像一朵盛开的红牡丹,在夜空中格外耀眼。沈复举着手机,镜头对准篝火,弹幕瞬间被“震撼”刷屏:
“我的天!这也太壮观了!三层楼高的篝火,第一次见!”
“牡丹火!真的像牡丹!李阿爷的手艺绝了!”
“好热闹啊!我能听到人群的欢呼声,羡慕死了!”
“撒松香!快撒松香!让火焰再旺一点!”
老沙拿出买好的松香,往火焰里撒了一把。“噼啪”一声,松香遇火爆燃,火焰瞬间蹿高了好几米,引得人群又是一阵欢呼。白族的小伙子们弹起了大三弦,姑娘们唱起了山歌,大家围着篝火跳起了舞,整个洋人街都变成了欢乐的海洋。
沈复放下手机,跟着阿秀一起跳舞。他从未如此放松过,明代时的礼仪束缚、穿越后的迷茫焦虑,在这炽热的火焰和欢快的歌声中,似乎都被烧得一干二净。他想起芸娘曾说,希望他能“活得自在些”,不要被世俗的规矩困住。或许,此刻的狂欢,正是芸娘希望他拥有的样子。
跳累了,沈复便沿着篝火旁的小摊闲逛。忽的,一本泛黄的线装诗集映入眼帘——摊布上摆着寥寥几本手写册子,封面是粗糙的牛皮纸,用炭笔写着“如风集”四个字,字迹狂放不羁。摊主正是个流浪诗人,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粗布衬衫,头发乱糟糟的,满脸胡茬,手里举着个土陶碗,正大口大口地喝着酒,眼神里满是醉意,却又透着几分清醒。诗集旁还放着支磨秃的毛笔,砚台里的墨汁尚未干透。
沈复俯身拿起诗集,指尖触到粗糙的纸页,竟觉比宫中宣纸更有筋骨。翻开第一页,“火把烧红洱海月,山风写尽半生狂”的诗句跃然纸上,笔墨间的洒脱之气扑面而来。他心头一震,抬头看向诗人:“先生,此集售价几何?某愿购之。”
流浪诗人闻言抬眼,打量沈复片刻,见他虽着民族服饰,眉宇间却有文人风骨,不由笑了:“公子倒是识货。这集子不卖钱,换碗米酒便好。”他指了指旁边的小酒桶,“刚温的米酒,配着诗读,更有滋味。”沈复欣然应允,叫摊主打了两碗米酒,在诗人对面坐下,将诗集捧在手中:“先生此诗‘山风写尽半生狂’,当真写活了大理的风骨。某沈复,祖籍苏州,见先生诗才,心生敬佩。”
诗人接过米酒,喝了一大口,抹了抹嘴:“沈复?倒是个雅致的名字。我以前在大学里教中文,后来嫌格子楼闷得慌,便背着笔砚四处走,走到大理,便把魂丢在了这苍山洱海里。”他指了指诗集,“这些句子,都是山风、篝火、洱海月教我的,比课堂上的平仄有趣多了。”
沈复心中一动,将诗集翻到“自由篇”,指着“墨池困不住诗魂,不如踏月逐山风”一句问道:“柳先生,某见此句,便知您对‘自由’二字颇有体悟。某曾以为,人生当有一番事业,方能不负此生。可看先生以山为纸、以风为笔,却又觉得自由或许更可贵。”
柳先生接过诗集,指尖摩挲着自己的诗句,眼中闪过一丝暖意:“公子是做什么事业的?看你气质,倒像个读书人,却又举着个会发光的手机,到处拍来拍去。”
“某是个网络主播,”沈复解释道,“靠直播间乞讨为生。粉丝有十一万,也算是小有名气。可某时常困惑,这事业虽能让某立足,却也让某受了不少束缚——要按时直播,要迎合观众的喜好,有时甚至要违背自己的心意,讲一些热门却无深度的故事。”
流浪诗人笑了,指着篝火旁狂欢的人群:“公子看这些人,他们有的是老板,有的是打工的,有的是学生,平日里都被生活的规矩束缚着。可今天火把节,他们放下了工作,放下了学业,尽情地跳舞、喝酒,这就是自由。事业和自由,本就是对立的,关键看你想要什么。”
“那先生觉得,哪个更重要?”沈复追问。他想起自己穿越到现代后的日子,为了直播事业,他学用手机,学看数据,学迎合观众的喜好,虽然收获了粉丝和认可,却也时常觉得疲惫。他怀念明代时和芸娘一起“闲时与你立黄昏,灶前笑问粥可温”的日子,那种自由,是现在的事业给不了的。
“对我来说,自由是一切。”流浪诗人望着跳动的篝火,眼神里满是醉意,却又格外明亮,“我教了二十年书,评职称、发论文、应付检查,每天都活得像个陀螺。直到有一天,我在课堂上想不起‘明月松间照’的下句,满脑子都是‘核心期刊’‘影响因子’,我才明白,我丢了自己。”他从布包里掏出另一本诗稿,递给沈复,“你看,这是我辞职后写的第一首诗,写的是黄山的日出,比我以前写的所有‘获奖诗作’都有灵气。”
沈复接过诗稿,翻开第一页,上面写着:“挣脱墨水瓶的束缚/我终于学会用山风写诗/日出时,云海翻涌/那是天地间最自由的韵脚”。字迹潦草,却透着一股洒脱的灵气,比那些堆砌辞藻的“文人诗”更有力量。
“可先生这样,没有稳定的收入,没有固定的住所,难道不觉得辛苦吗?”沈复问道。他想起自己刚穿越时,身无分文,住在最便宜的客栈,每天都要为生计发愁,那种辛苦,他不想再经历第二次。
“辛苦是自然的。”流浪诗人坦然道,“我睡过火车站的候车室,吃过最便宜的泡面,被人当成疯子驱赶过。可我不后悔,因为我找回了自己。事业能给你物质的安稳,却不一定能给你精神的自由;自由或许会让你物质匮乏,却能让你活得通透。就像这火把,它燃烧自己,看似是毁灭,实则是用火焰照亮了黑夜,这就是自由的力量。”
沈复沉默了。他想起自己的直播事业,虽然能给他人讲传统文化,传播芸娘的故事,却也让他受了不少束缚。有一次,他想给观众讲《三白游记》里他和芸娘“芸娘扮男装逛庙会”的故事,却被运营提醒“太冷门,没人看”,让他改讲“天鹅古堡探险的惊险片段”。他最终改了内容,虽然收获了更多的礼物和粉丝,却也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
“公子,你心里有执念。”流浪诗人突然开口,打断了他的思绪,“我从你翻诗时的眼神里看出来了,你怀念过去,怀念某个人,某段时光。你做直播事业,看似是为了传播文化,实则是为了逃避过去的光影。”
沈复的心猛地一跳,像被人看穿了心事。他想起芸娘,想起那些和她一起度过的日子,那些日子像刻在骨子里的烙印,无论过了多少年,都无法忘记。
“某的妻子芸娘,遗留在明代了。”沈复轻声说,声音带着几分哽咽,“某穿越到现代,某的事业,是为了她,也是为了自己的执念。”
流浪诗人看着他,眼神里满是理解:“执念是好的,它能支撑你走过最艰难的日子。可执念太深,就会变成束缚,像一根绳子,捆住你的心。你看这篝火,它不会执着于‘过去是松木’,它只是尽情燃烧,用火焰温暖他人;你看这风,它不会执着于‘过去是山涧的清泉’,它只是自由地吹,带来花香和凉意。”
他喝了一口酒,突然看着沈复的眼睛,一字一句地说道:“公子,人生如能遗忘过去 , 也是一种福气。”
沈复猛地愣住了。这句话像一道惊雷,在他的心里炸开。他一直以为,记住芸娘,记住过去,是对芸娘最好的怀念,也是他活下去的意义。可诗人的话,却让他开始怀疑——如果遗忘过去是福气,那他一直坚守的“执念”,到底是对还是错?
篝火渐渐弱了,狂欢的人群也渐渐散去。沈复和朋友们走在回客栈的路上,夜色里,古城的青石板路泛着月光的清辉,路边的灯笼还在亮着,暖黄的光映着他的影子,拉得老长。
“三白,你怎么了?从刚才就一直闷闷不乐的。”阿秀看出他的异样,轻声问。
“某没事,只是在想那位流浪诗人说的话。”沈复轻声说,“他说,人生如能遗忘过去 , 也是一种福气。某一直以为,记住芸娘是对她最好的怀念,可他的话,让某很困惑。”
沈复沉默着,走到洱海边。夜色里的洱海像一面巨大的镜子,映着满天的繁星。他想起芸娘生前最喜欢看星星,她说,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逝去的人,他们在天上看着自己爱的人。他摸了摸怀里的《三白游记》初稿,那是他用毛笔写的,上面记满了他和芸娘的故事。
“芸娘,你说,某该怎么办?”他轻声问,声音被风吹散在洱海里。他仿佛看到芸娘站在洱海边,穿着她最喜欢的蓝布裙,笑着对他说:“三白,好好活着。”
夜色渐深,洱海的风轻轻吹过,带着淡淡的咸味。沈复关掉直播,和朋友们一起往古城走。远处的火把还在燃烧,像一颗温暖的星,照亮了他前行的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