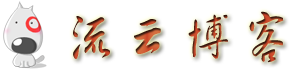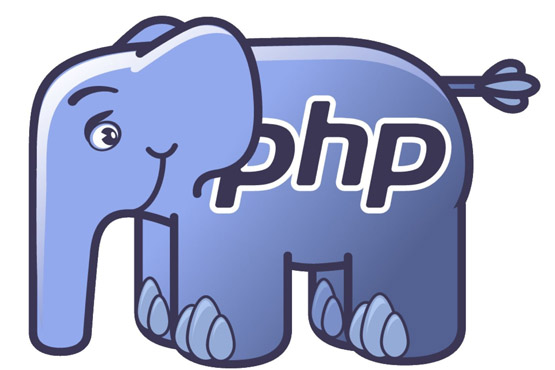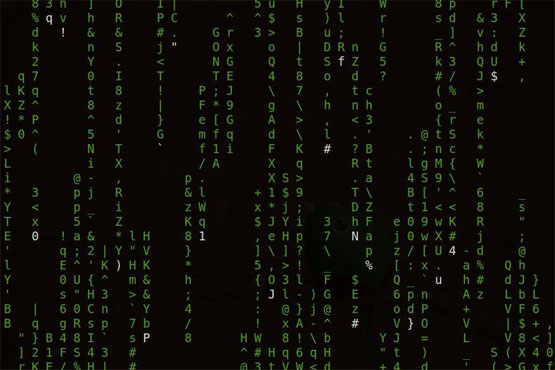大理的晨光总带着苍山雪水的清冽,透过“月明小筑”酒馆的雕花木窗,在沈复手边的诗稿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那本泛黄的《如风集》摊开在酸枝木桌上,“能遗忘过去是一种福气”这行字被他用朱笔圈了又圈,墨迹晕开,像极了明代苏州梅雨季里浸潮的宣纸。

他指尖摩挲着粗糙的麻纸页,眼前又浮现出火把节当晚流浪诗人的模样——乱发如蓬,胡茬间还沾着洱海的潮气,粗布衫领口磨出毛边,可那双醉意朦胧的眼睛里,藏着比洱海底的月光更通透的清明。沈复自万历年间穿越而来,每日以直播为业,念着芸娘的笑、苏州的雨、拙政园的兰,从未想过“遗忘”竟能与“福气”挂钩。那些刻在骨血里的记忆,若真能轻易抹去,他这“沈三白”的名号,又还有什么分量?
“三白,发什么呆呢?鸡丝米线都要凉透了!”阿秀端着个青花瓷碗上楼,碗边摆着碟油鸡枞,金黄的油光映着她腕间的银镯子,叮当作响,“良源刚从才村拍日出回来,说今日洱海上飘着晨雾,像裹了层纱,你要是开直播去拍,保准能上平台推荐位。”
沈复抬眼,见良源正蹲在墙角擦拭相机镜头,镜面上还映着洱海的橘色晨光。他把诗稿轻轻推到一旁,舀了勺米线,鲜美的鸡汤在舌尖散开,却压不住心头的滞涩。“阿秀姑娘,良源兄,”他放下竹筷,声音带着彻夜未眠的沙哑,“柳先生那句‘能遗忘过去是一种福气’,某思来想去,终是不解。
良源停下擦镜头的手,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:“公子是困在‘铭记’与‘遗忘’的执念里了。流浪诗人是浪迹山河的高人,他的‘遗忘’或许不是真的忘却,而是放下牵绊。只是这话终究是他的感悟,咱们隔着身份境遇,猜再多也无用。”
“对啊!”阿秀突然拍了下手,鸡汤溅起几滴在靛蓝的扎染桌布上,她浑然不觉,眼睛亮晶晶地说,“解铃还需系铃人啊!流浪诗人既然能说出这话,肯定有他的道理。你去找他问个清楚,不比自己闷在心里瞎琢磨强?他昨晚在洋人街的篝火旁卖诗集,今天说不定还在古城里打转呢!”
“解铃还需系铃人……”沈复反复咀嚼着这七个字,只觉得心头像被苍山的风劈开一道豁口,豁然开朗。是啊,他困在自己的文人执念里,把简单的道理想得千回百转,不如直接找到流浪诗人,当面请教个明白。他猛地站起身,抓起桌上的手机稳定器:“某这就去找他!良源兄,你陪某一起,顺便拍些古城晨景素材。”
“放心去吧!”阿秀从柜台下摸出个油纸包,塞进他怀里,“这里面是刚烤好的喜洲粑粑,甜口的,揣在怀里暖着,饿了就吃!
沈复刚跨出酒馆门槛,就被老沙从烤架后叫住。老沙举着把刷油的刷子,指了指他怀里的稳定器:“三白,开着直播找!你那十几万粉丝遍布古城,比咱们俩瞎找管用多了!”
沈复恍然,立刻点开直播软件。镜头刚对准青石板路上的晨光,弹幕就像潮水般涌了进来:
“沈公子早啊!今天是要讲《闲情记趣》里才子佳人的故事吗?”
“昨晚火把节的流浪诗人好有风骨!沈公子是要去找他对诗吗?”
“求偶遇!我正在洋人街的‘猫的天空之城’,沈公子快来!”
沈复对着镜头拱手作揖,棉麻衫的袖口扫过镜头边缘:“诸位乡亲父老,今日某暂不讲故事,要去寻找昨晚的流浪诗人。他一句‘能遗忘过去是一种福气’,某未能参透,今日特去请教。若有乡亲在古城见到一位乱发胡茬、肩背布包、卖手写诗集的先生,还望在弹幕告知。”
洋人街的晨雾还未散尽,青石板路上已有些许行人。路边的咖啡馆刚拉开折叠门,店员正用抹布擦拭户外桌椅,咖啡豆的焦香混着洱海的潮气飘过来;扎染店的白族阿婆把蓝白相间的布料挂在竹竿上,风一吹,像翻涌的浪头拍在青瓦白墙上。沈复举着稳定器,镜头缓缓扫过街边的摊位,目光在每个卖手工艺品的小摊前停留。
“公子,昨晚流浪诗人就是在前面那个转角摆摊的。”良源指着不远处的大槐树,树底下摆着几个小摊,有卖银饰的、卖明信片的,还有个捏面人的老师傅,唯独没有那本熟悉的牛皮纸诗集。
沈复快步走过去,对着捏面人的老师傅拱手:“这位老丈,请问您见过一位卖手写诗集的流浪诗人吗?昨晚他还在此处摆摊,粗布衫,乱头发。”
老师傅抬起头,皱纹里嵌着面灰,指了指东边的路口:“你说那个喝着酒写诗的先生啊?就背着布包往人民路去了。他说人民路的晨光斜照在老墙上,最适合写意境诗句。”
“多谢!”沈复连忙道谢,镜头转向老师傅案上的面人——竟有个捏成他《三白游记》时的模样,头戴方巾,手持书卷。弹幕立刻炸开:
“哇!这面人捏的是沈公子吧!太像了!”
“老师傅手艺绝了!地址在哪?我要去定做一个芸娘的!”
“人民路我熟!我在‘大冰的小屋’门口守着,看到柳先生立刻报信!”
往人民路走的路上,沈复的镜头不时扫过街边的风景。一家古籍修复店的木窗半开着,老板正用鸡毛掸子拂去线装书的灰尘,阳光照在泛黄的书页上,像撒了层金粉;街头艺人抱着吉他弹唱《去大理》,歌声里满是慵懒的烟火气;穿汉服的姑娘提着裙摆走过,广袖流仙裙与青瓦白墙的古建筑相映成趣,引得路人纷纷拍照。
“公子,你看那边!”良源突然拽了拽他的袖子。沈复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,只见人民路的街边,摆着个简陋的小摊,摊上垫着块蓝印花布,上面整齐地码着几本牛皮纸诗集,封面的“如风集”三个字苍劲有力——正是流浪诗人的诗集!
沈复心头一喜,快步走过去。可走近了才发现,摊位后坐着的不是流浪诗人,而是个穿校服的小姑娘,扎着马尾辫,手里还捏着支铅笔在草稿纸上画速写。“小姑娘,这诗集是主人在吗?”沈复轻声问,生怕吓着她。
小姑娘抬起头,脸上带着腼腆的笑:“叔叔好,这是流浪诗人的诗集。他今早把诗集放我这儿代卖,说要是有位穿棉麻衫、像古代读书人的叔叔来找他,就把这涨纸条送给你。
沈复凑过去,只见纸条上写着:“山寻云迹,水寻月影,人寻过往,终困樊笼。风无迹,月无声,忘川不渡,自在为峰。”字迹狂放,墨色浓淡不一,显然是即兴所作。
“他这是在点化某啊。”沈复摩挲着揣摩,镜头扫过人民路的青瓦屋顶,“家人们,五华楼是古城的制高点,站在上面能俯瞰整个大理城,流浪诗人说不定在那里喝酒吟诗。”
弹幕里立刻有人回应:“五华楼我刚去过!楼前有个卖烤乳扇的阿婆,我帮沈公子问问!”“我在五华楼的台阶上坐着,看到穿粗布衫的立刻喊!”“沈公子快去吧!我们帮你盯着弹幕!”
走到五华楼脚下时,晨光已驱散了最后一丝雾气。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城楼,青瓦飞檐,斗拱交错,楼前的广场上,几位白族老人正在打太极,动作舒展如流云。沈复沿着石阶往上走,每一步都踩在历史的回响里——明代时他曾登过苏州的北寺塔,那时是与芸娘一起,看满城烟柳;如今登五华楼,身边是良源,镜头后是十几万素未谋面的粉丝,物是人非,心境却有几分相似的开阔。
沈复登上五华楼远远望去,苍山十九峰如黛,山顶的积雪在晨光中泛着银光;洱海如一块巨大的碧玉,倒映着蓝天白云,古城的青瓦白墙在水边铺展开来,像一幅活的水墨画。“各有千秋。太湖温婉,如芸娘的绣品;洱海开阔,如流浪诗人的诗句。”
可午夜梦回,他总会想起芸娘临终前的模样,想起自己未能陪她看遍山河的遗憾,那些回忆像藤蔓,紧紧缠住他的心脏,让他不敢轻易触碰四百年后的新生活。
良源说道“芸娘若在,是想让你每天活在回忆里唉声叹气,还是想让你看遍这四百年后的山河,活得自在通透?”
这句话像一道惊雷,炸得沈复心神剧震。他想起芸娘生前常说的“愿君活自在,不负少年时”,想起她扮男装陪他逛庙会时的洒脱,想起她把兰草绣在帕子上时说的“草木有本心,何求美人折”。芸娘从来不是个困于闺阁的女子,她的通透,比他这个读圣贤书的文人更甚。
沈复若有所悟,他翻开诗集,找到《扎染》这首诗:“白布浸蓝,线缚千缠。解缚时,花自蔓延。心若如布,何惧纠缠?忘缚忘花,方得清欢。”字迹狂放,却字字戳中他的心事。
从五华楼下来,沈复的心情比来时更沉。他坐在楼前的石阶上,反复读着《扎染》这首诗,直播间的观众也安静下来,弹幕里满是安慰:
“沈公子别难过,流浪诗人肯定是想让你自己悟透。”
“芸娘姐姐肯定希望沈公子活得开心,不是吗?”
“要不沈公子去喜洲看看?流浪诗人提到了扎染,喜洲的扎染最有名!”
“对!喜洲的粑粑超好吃,沈公子去尝尝,说不定心情就好了!”
良源拍了拍他的肩膀:“公子,既然说喜洲扎染能给你启示,咱们就去看看。喜洲离古城不远,租辆电单车环海过去,既能拍些好素材,又能让观众看看大理的非遗文化,说不定还能偶遇柳先生。”
沈复点头,站起身。他知道良源是想让他转移注意力,可心里的结,终究要自己解开。两人在古城门口租了电单车,车筐里放着那本《如风集》和阿秀给的喜洲粑粑,往喜洲方向骑去。环海西路的柏油路两旁,格桑花开得肆意,粉的、紫的、白的,被风吹得像波浪,偶尔有海鸥从洱海上掠过,发出清脆的叫声。
“公子,镜头扫一下洱海!”良源骑着车,侧头喊道。沈复依言调整稳定器角度,波光粼粼的洱海瞬间填满屏幕,弹幕瞬间活了过来:
“哇!这风景也太美了吧!像闯进了水墨画里!”
“我去年环海骑行过,累到瘫倒,但看到这样的风景瞬间治愈!”
“前面就是喜洲了!看到那些青瓦白墙的房子了吗?那是喜洲的白族民居!”
骑到喜洲古镇时,已是正午。古镇的入口处,几位白族阿婆正坐在大青树下卖扎染布,蓝白相间的布料挂在树枝上,像一片流动的蓝色云霭。沈复停下车,走到一位戴银饰的阿婆摊位前,笑着问:“阿婆,您见过一位穿粗布衫、卖手写诗集流浪诗人吗?他说喜洲的扎染能给人启发。”
阿婆抬起头,脸上的皱纹里满是笑意,指了指摊位后的竹椅:“以前有个喝醉酒的流浪诗人在我这儿买了块兰草纹的扎染布,说要做个书套,还跟我聊了会儿扎染的手艺。”
“他还跟您说什么了?”沈复连忙追问,镜头对准阿婆手里正在扎的白布,“诸位乡亲,这位阿婆正在做扎染,你们看,她用棉线把白布扎成兰草的形状,染出来就是芸娘最爱的纹样。”
“他说,扎染这东西,讲究‘缚之愈紧,染之愈深’,可要是一直不松线,就永远是块皱巴巴的布,成不了好看的花纹。”阿婆拿起一把剪刀,小心翼翼地剪开扎线,“你看,要先缚,再染,最后解缚,花纹才会舒展开来。人啊,也一样,心里的结要是不解开,再好的日子也过不舒展。”
沈复盯着那块刚解开的扎染布,兰草纹样在蓝底上舒展开来,疏密有致,浑然天成。他突然想起流浪诗人的诗“解缚时,花自蔓延”,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——流浪诗人是想说,他对过去的执念,就像扎染的棉线,若不松开,永远得不到真正的自在。
沈复谢过阿婆,买了两块扎染桌布——一块送阿秀,一块留着铺在直播的桌子上。良源笑着说:“公子,不远处才村的渔火夜景很有名,正好拍些素材,晚上直播的时候用。”
两人骑着车往才村去,路过喜洲的四方街时,沈复特意买了十个喜洲粑粑,甜咸各半,装在油纸包里揣着。弹幕里的观众看得直流口水:“沈公子太会了!求代购!”“甜口的最好吃!配着梅子酒绝了!”“等下直播吃粑粑吧!我们要看吃播!”
才村码头的风很大,吹得人衣袂翻飞。渔民们正忙着收网,渔网从水里拖上来,带着晶莹的水珠,银鳞般的小鱼在网里跳跃。沈复找了块礁石坐下,打开直播,镜头对准波光粼粼的湖面:“诸位乡亲,咱们现在在才村码头,也许流浪诗人这里看渔火。等下日落时分,渔民会点亮渔灯,整个湖面都会亮起,像撒了满地星星。”
他一边和观众聊天,一边留意着来往的行人。夕阳渐渐西沉,把洱海染成了橘红色,渔民们的渔灯一盏盏亮起,真的像星星落在了水面上。可直到暮色四合,流浪诗人身影也没有出现。良源递过来一瓶水:“公子,流浪诗人可能去古城夜市喝酒了,咱们回去吧,不然阿秀该担心了。”
沈复点头,心里却有些怅然。他关掉直播,和良源骑着车往古城回走。环海西路的路灯亮了起来,暖黄的灯光映在柏油路上,像一条延伸的星河。路边的稻田里,蛙鸣此起彼伏,混着远处古城的喧嚣,构成了大理最温柔的夜色。
回到大理古城门口时,已是晚上八点。夜市早已热闹起来,火把形的灯笼挂满了街道,烤乳扇的香味、炸洋芋的辣味、梅子酒的清香混在一起,勾得人食欲大开。沈复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,沿着夜市边缘慢慢走,怀里的喜洲粑粑业已微凉,他却没什么胃口。
良源去给阿秀发消息,让她留些饭菜,沈复独自站在古城的大照壁前。照壁上“文献名邦”四个大字在灯光下熠熠生辉,映着他孤单的影子。他想起流浪诗人的诗,想起阿婆的扎染,想起芸娘的笑,心里像堵着一团湿棉花,沉重又闷痛。他知道大家都在点化他,可那些刻在骨血里的记忆,怎么可能说放下就放下?
“家人们呐!你们看这古城夜景,是不是比白天更有味道!”一阵洪亮的声音突然从旁边传来,带着麦克风的扩音效果,“等下咱们去吃烤乳扇,我跟你们说,大理的烤乳扇裹上玫瑰酱,好吃到哭!”
沈复抬头望去,只见不远处围了一群人,中间站着个穿户外冲锋衣的年轻人,手里举着个专业稳定器,镜头前还架着补光灯。年轻人皮肤黝黑,笑容爽朗,身后跟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姑娘,手里拿着个笔记本,正快速记录着什么。周围的观众举着手机拍照,嘴里喊着“小白老师”。
“是户外大主播小白!”良源正好回来,一眼就认出了他,“他粉丝上百万,是平台直接签约力推的,我之前还看过他去大漠英雄会的直播,非常精彩!”
小白也注意到了人群外的沈复,眼睛一亮,立刻拨开人群走过来:“您是‘沈三白’的沈公子吧!我看过你上一期的天鹅古堡探险真的是惊险万分扣人心弦!”他对着自己的镜头说,“家人们,你们看谁来了?是我的偶像沈公子!”
小白的直播间瞬间炸了,礼物特效刷个不停:
“哇!双厨狂喜!我的两个宝藏主播同框了!”
“沈公子好有气质!比直播里更有文人风骨!”
“小白快问问沈公子,能不能一起直播!想看你们聊大理文化!”
沈复对着小白的镜头拱手:“小白兄客气了,某也看过你的直播,你的大漠之行,让某见识了祖国山河壮阔。”
“沈公子过奖了!”小白热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,指着身后的姑娘介绍,“这是我的助理阿桑,负责节目策划和场地考察,我们这次来大理,是为了筹备一档叫《向往的大理》的综艺直播节目,提前踩点选场地。”
阿桑走上前,递过来一张名片,笑容干练:“沈公子您好,我是阿桑。我们做过您的直播数据分析,您的观众群体和我们综艺的目标受众高度契合,一直想找机会合作。”她指了指古城夜市,“我们正考察夜市的场地,想在火把节期间做一场民俗主题直播。”
沈复接过名片,指尖触到光滑的纸页,心里有些恍惚。他还沉浸在寻找流浪诗人的怅然里,没想到会突然遇到同行,甚至收到合作邀约。小白看出他神色不对,拉着他走到旁边的烤乳扇摊位前:“老板,四串烤乳扇,都裹玫瑰酱!”转头对沈复说,“沈公子,看你脸色不好,是不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?跟我说说,说不定我能帮上忙。”
烤乳扇的香味飘过来,沈复叹了口气,把寻找流浪诗人的经过和自己的困惑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小白听完,咬了一口烤乳扇,笑着说:“沈公子,我以前是做夜场DJ的 , 直播行业兴起后 , 辞职转行做起了户外主播。刚开始粉丝只有几百个,吃了上顿没下顿,可我觉得比以前开心多了。流浪诗人说‘能遗忘过去是一种福气’,不是让你忘记芸娘,是让你忘记‘遗憾’这种情绪。”
阿桑补充道:“沈公子,我们也做过文化类直播,发现最打动人的不是沉浸过去的伤感,而是带着过去的美好往前走的坚韧。芸娘是您生命里的光,但您不能只守着光的影子,您要带着这束光,去照亮更多人。”
“对!”小白拍了下手,指着夜市里的人群,“你看这些人,有本地的老人,有外地的游客,有带着孩子的夫妻,他们都在享受当下的快乐。流浪诗人说的‘遗忘’,是让你放下‘没能陪芸娘看遍山河’的遗憾,带着她的爱,替她看遍这四百年后的世界。这才是对她最好的怀念啊!”
“无拘无束,才是人生真意。”小白看着他的眼睛,认真地说,“你看你的粉丝,他们喜欢的不是你的伤感,是你讲的故事里那份对生活的热爱。”
沈复愣住了,手里的烤乳扇渐渐凉了,心里的郁结却像被风吹散的雾。他想起流浪诗人的诗,想起阿婆的扎染,想起弹幕里粉丝的鼓励,突然明白了——遗忘不是背叛,执念才是枷锁。芸娘若在,定会希望他活得自在通透,而不是困在回忆里自怨自艾。
“多谢小白兄,多谢阿桑姑娘。”沈复举起手里的烤乳扇,像举着酒杯,“某明白了。”
就在这时,阿秀的消息发了过来:“三白!等你回来喝酒!”
沈复眼睛一亮,转头对小白和阿桑说:“小白兄,阿桑姑娘,某有位故人在酒馆等某,不如一起过去坐坐?咱们聊聊合作的事,谈谈对大理的向往。”
小白和阿桑相视一笑,异口同声地说:“求之不得!”